永远怀念杨竞初先生!
我们敬爱的杨竞初先生溘然长逝,岭南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及校友深感悲恸。杨竞初先生是岭南学院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一生心系教育,以毕生心力守护岭南,是岭南精神最热情的传承者。他的谦逊与热忱,让每位校友感受到岭南大家庭的温暖。
先生虽逝,其精神早已融入岭南人心灵深处,“殷红如血”的赤诚与“深灰似铁”的坚韧,将指引所有岭南人前行,作育英才,服务社会,让岭南精神生生不息。
下文为2019年岭南本科生对杨竞初先生的采访,字里行间,先生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对新一代岭南人的深切期望萦绕耳畔。
岭南故事 | 杨竞初:遇物不竞,初心未改
杨竞初,岭南学院董事会董事,曾主持修建岭南学院十三栋院楼,目前负责海内外校友联络委员会事宜。

仲夏的龙舟水来势汹汹,时刻不休地冲刷著五岭以南的广袤大地。沉静地坐落在中山大学北区一隅的荣光堂,在雨中显得格外古朴、典雅,意蕴悠长。来到荣光堂时离原定的采访时间尚有二十分钟,但杨竞初先生却比记者们来得更早。年过七十的他不见黑发,却仍然显得精神矍铄,充满热情。他抱著厚厚的采访材料,轻车熟路地领着记者们进入会议室。透过摆放着花草的玻璃窗向外望去,雨中的校园显得格外宁谧。
就在这里,杨竞初先生将他与岭南结缘的大半生娓娓道来。
“岭南书院全面的博雅教育影响了我”
1967年9月,岭南校友在香港成立岭南书院有限公司以筹办书院,开始了岭南大学复校的第一步,而杨竞初先生也在完成六年岭南中学教育的机缘之下进入岭南书院,成为第一批学生。杨先生和岭南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谈及在岭南书院的学习生活,杨先生笑言不过稀松平常,但言语间又时刻流露出对旧日时光的怀念。中学时代岭南为每个学生都提供住宿,这在当时的香港并不多见。学生们也因此要自己料理生活起居,还要栽培校园里的花草。在年轻气盛的学生们看来,这些杂务显得繁杂而无用,但正是当时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提高了杨竞初先生的能力。他笑道:“但还好当时都有做,所以现在才什么都能做。”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在学习历史专业的同时半工半读,做装修设计方面的工作。而这么多年来,他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中学时代每周三下午三点的“做人课”。在短短四十五分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人生道理,对他之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岭南书院的博雅教育让他能够用更加广泛而全面的视野看待问题,减少了许多当局者迷的困境。
“每一栋楼都有辛酸苦辣”
1985年,伍沾德先生出任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主席时提议在广州康乐恢复岭南教育,而作为岭南有生力量的杨竞初先生,也受邀参与到重建工作中来。香港、澳门及美加的许多校友出资出力,终于在三年后的11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通过国家教育委员会及国务院审批而正式成立,次年开始招生。

刚复建的岭南学院可说是一穷二白。偌大的土地上一片荒芜,蚊虫猖狂,野草疯长,人员出入仅能通过破败的小北门。现在岭南学院所处的北区,当初只有孤零零的两栋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的十二年间,十三栋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设起来,至今仍接受着风雨的考验。
最初参与重建工作时,杨竞初先生仍在银行工作,留出星期天为岭院主持建筑装修工程,后因无法兼顾而开办装修公司,将所有精力投入建筑工作中。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预算有限,物资也很匱乏。提及这段经历,杨竞初先生感叹道:“在当时的中国,要建一栋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为了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杨先生亲力亲为,自己操办一切。从设计建筑图纸到向国外进口优质材料,就连建筑人才也由他从香港招揽。杨先生为建楼到处奔波,最终得到了董事会的信任:“没有杨先生签名不给钱”。这简短的一句话却似有万钧之重,这既是对杨先生工作成果的认可,又是对他人格的信任。于是林护堂、黄传经堂、伍舜德图书馆,叶葆定堂……这些现在岭院学子们习以为常地进出的建筑就在他的主持下建造起来。“每一栋楼背后都有许多故事可讲。”杨竞初先生抚摸着荣光堂的木制墙面,感慨地向我们诉说起那些建筑在诞生之初的故事。
如今每个岭南学子进入大学校园都要拜访的岭南堂落成于1999年。它是岭南建筑大师佘畯南和莫伯治先生的作品,其设计灵感来源于南方良渚文化的玉琮,以绿色玻璃为外墙,造型外方内圆。这富有现代特色的建筑在古色古香的康乐园里独树一帜,体现着古今冲撞与交融。
现坐落于惺亭旁的乙丑进士牌坊,虽然距离稍远,但其实也与岭院有关。这座牌坊是原来广州城内“四牌楼”中的一座,在上世纪40年代由于广州市政府要扩建马路,把其中一座赠送给岭南大学,选址在格兰堂东侧。在十年浩劫中,牌坊被毁,幸运的是大部分石构件都被保存了下来,最终在1999年由岭南校友捐资70多万元进行重修,并被迁移至惺亭西侧。杨竞初先生说这是当时的学院书记注重教育,为了树立学术风气,恢复岭南传统而力争重建的。础柱庄雄的进士牌坊,也正昭显着岭南人独有的气节和志向。
而提及同样是在1999年建立的教授楼,杨竞初先生说他当时力争要加上国内建筑从未做过的“三样”:八层楼设置电梯、门禁闭路电视、楼梯上的马赛克装饰。这样的想法在当时为许多人不解并反对,觉得这是浪费预算的设计。但20年后,多栋楼重修时再加电梯已经需要更高的费用,美观而坚固的马赛克墙面也经受住了时光的流逝。那些当初反对杨先生的人,如今也不得不认同他的远见卓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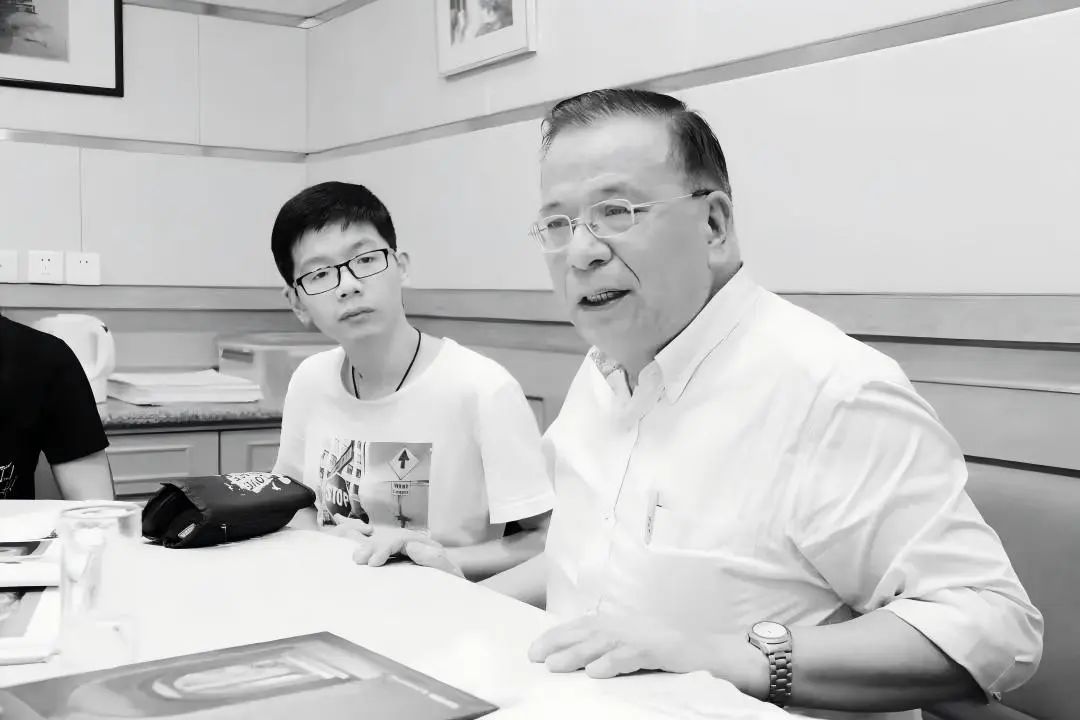
除了建造院楼,杨竞初先生在其他方面也对岭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岭院MBA最初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办学,但学生没有教材,杨先生便和几位校友每年亲自从美国寄来三十套左右教材,每套三至四本,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从香港带来广州。这些教材为岭院第一届MBA学生所用,陪伴他们度过了最初的时光。
“岭南人都是‘蠢材’”
许多岭院的新生认识杨竞初先生都是在刚入学时教唱岭南歌曲的大会上。他不仅亲自教新生唱校歌,就连所使用的11首岭南歌曲也是由他精选,并录制成卡拉OK版的。这些或激昂或抒情的歌曲,滥觞于岭南学子在康乐园旦夕辟荒、载歌载学的时期。时光荏苒,载体也由歌谱变为CD,但其中凝结着的岭南红灰精神却传承至今,从未褪色。
而谈及岭南精神,杨竞初先生也有许多话要说。
他感恩所有付出过的岭南人,在有想要拆除康乐园西区的岭南墓园的声音出来时,他坚决反对,因美国传教士“一生奉献中国教育”,在岭南最终辞世。他努力为公,服务社会,而这坚定的信念来自上一辈岭南人的讲话。“这世界上有三‘才’:钱财,人才,蠢材。钱财没了可以再赚,人才也比比皆是,但蠢材绝不多见。而岭南人,都是蠢材。”因为他们不计较得失,不讲求代价,为国为民,奉献一生。这对他触动很大,也更坚定了他为社会服务的信念。
岭南精神影响了他,他也践行着岭南精神。
他说:“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有人试图拿杨先生的名片得到在荣光堂住宿的折扣,却得知名片无用,愤愤而去;杨竞初先生来荣光堂吃饭,从来都按菜单上的价格支付费用,即便是一杯咖啡也不例外。
他注重诚信,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和别人约定相见时,自己于约定时间前到达也不会告知对方,而若是有迟到的可能,他一定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就向对方报备。
“你们也随时可以约我,但只有星期四不行。”杨先生笑道。这是他和老一辈岭南人每周聚会的时间,十几年来风雨无阻。即使与会人员从最初的十五人,已经减少到现在的四五人;那些曾经壮志凌云的青壮年,也都白了鬓角,需要护工陪伴。但在聚会上和老先生们畅谈学院最近的动向时,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三十多年来所投注的心血都是有回报的。
对他而言,来到岭院就像回到自己的家。而岭南学子们也是他关心的对象。为了学生们能四年都在古朴幽雅的康乐园中生活学习,校友会向学校争取了整整十年,这最终在2017级得到落实;他关心岭南学子的宿舍条件,力争为同学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在他心中,是这片土地将大家凝聚在一起,岭南就是一个大家庭。
而对于这大家庭中的新一代岭南人,他希望岭南学子们都能脚踏实地,独立自主,吐故纳新,全面发展,成为服务社会的英才。

采访结束后,记者们和杨先生在荣光堂共进工作餐。杨竞初先生最初并不打算用餐,记者们在追问下才得知前几日杨先生突发面瘫,被建议晚上应减少进食。他说:“我那时候想,我还不能倒下去,岭南还需要我。”这让记者们都十分触动。
江水滔滔,盖不住岭南故事的声声回响;微风阵阵,吹不散岭南人的颗颗红心。栋栋院楼离不开杨先生的辛勤奔波,即便是叶葆定堂一张简单的椅子也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三十多年一晃而过,如血如铁的红灰精神仍在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间传递延续,熠熠生辉。




